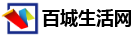海伦凯勒故事 海伦凯勒的励志故事简短

海伦·凯勒的故事(海伦·凯勒的励志故事很短)
在学习的过程中,海伦·凯勒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个失去听力和视力的女孩是如何完成数学、天文、希腊语等科目的学习,最终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的?
突破逆境
作者:海伦·凯勒
摘自《如果你给我三天光明》
我在剑桥中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然而,在最初的几周,我们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个学年应该主修数学,除了天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可惜课程已经开始了,我需要的很多书都没能及时拿到活版,同时也缺少一些课程必备的重要学习工具。再加上我班学生多,老师也不能给我特别的指导。沙利文小姐必须为我读完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解释。她灵巧的双手不再胜任这项任务,这是11年来前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要求在课堂上做,但我做不到。直到我们买了一台盲文打字机,我可以用它“写下”解决方案的每一步。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看不见。我理解几何图形概念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直的和弯曲的引线在垫子上制作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和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步骤,完全取决于大脑记忆。
总之,学习充满了障碍。有时候,我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还是会表现出这种情绪。到目前为止,我很惭愧错过了这个。尤其是回想起因为这个原因对沙利文小姐发脾气,我觉得特别惭愧。因为她不仅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为我奋斗过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消失了,字母书和其他学习工具也相继到来。我重拾信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理解,很多观点不能如我所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感到头疼。即使我在座垫上拼了很多数字,也分不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我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被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我的书到达之前,吉尔曼先生开始向沙利文小姐指出,我的课太重了,尽管我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我的课时还是减少了。
起初,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有必要,准备高考需要五年时间。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让沙利文小姐、哈珀女士(学校教务长)和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可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备考。起初,吉尔曼先生同意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作业进展不够顺利,他坚持要我再学习三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和其他学生一起上大学。
11月17日,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虽然沙利文老师向吉尔曼先生解释说只是小问题,但吉尔曼先生认为我的身体被作业压垮了,所以他彻底修改了我的学习计划,让我不能和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因为吉尔曼先生和沙利文小姐之间的分歧,我妈妈决定让我和我妹妹米·朱莉一起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妈妈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做我的导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2月至7月,基思先生每周去伦萨姆两次,教授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沙利文小姐担任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波士顿。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基思先生每周教我五次,每次一小时。先解释上节课没听懂的内容,然后布置新作业。他把我一周前用打字机做的希腊文练习带回去仔细修改,然后还给我。
我的高考准备一直是这样进行的。我发现单独听课不仅比上课听课更容易理解,也更轻松愉快,所以不需要跟在后面,也不会赶时间。老师有充足的时间解释我不懂的地方,不如学得比在学校快。在数学方面,我还是比其他课程有更多的困难。代数和几何比语言和文学容易一半!但即使是数学,基思先生教得也很有趣。他尽量减少问题和困难,这样我就能完全理解它们。他让我快速思考,严谨推理,冷静逻辑地找到答案,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思考。虽然我太笨了,甚至不能容忍约伯,但他总是那么温柔和耐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入学考试的期末考试。
第一天考基础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不允许沙利文老师为我读试卷,邀请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温妮先生为我把试卷翻译成盲文。我和文尼先生认识,除了盲文,我们不会说话。
盲文可以用于各种文字,但很难用于几何和代数。我筋疲力尽,灰心丧气,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尤其是代数。我真的很熟悉一般人会用的三种盲文:英语、语、纽约语,但几何和代数中的符号在这三种盲文中差别很大,代数中我只用英语盲文。
考试前两天,文尼先生给我发了哈佛大学老代数试题的盲文,不过是盲文。我赶时间。我会立即写信给文尼先生,请他解释上述符号。很快,我又收到了一张试卷和一张符号表。我开始学习这些符号。代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忙于一些复杂的练习,分不清括号、大括号和平方根的区别。基思先生和我都有点气馁,担心第二天的考试。考试的时候,我们提前到了学校,让文尼先生仔细给我们讲盲文的符号。
几何考试最大的困难是我习惯了把命题拼在手上。不知何故,虽然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用盲文看起来很乱。说到代数,难度就更大了。你刚刚学的符号自以为是,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就乱套了。另外,我看不到我在打字机上打的东西。我曾经用盲文计算,或者用心灵计算。Keith先生过于强调训练我的心算能力,却没有训练我怎么写试卷,所以我的答案很慢,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看试题,才知道怎么做。老实说,我现在不确定我自己是否已经读完了所有的符号。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真的太难了,但我不怪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迪肯先生不会意识到我的试题有多难,也无法理解我必须克服的特殊困难。
然而,如果他们无意中给我设置了许多障碍,我可以手淫,我终于克服了所有的障碍。
读者:王占琦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江淮iEV7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江淮汽车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人信息,...浏览全文>>
-
试驾MG4 EV全攻略:MG4 EV是一款主打年轻科技感的纯电紧凑型车,外观时尚,内饰简洁。试驾时重点关注其动力...浏览全文>>
-
预约试驾奥迪SQ5 Sportback,线上+线下操作指南如下:线上预约:访问奥迪官网或官方App,选择“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试驾别克君越,一键启动,开启豪华驾驶之旅。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君越以优雅外观、舒适空间和强劲动力赢得广...浏览全文>>
-
试驾沃尔沃XC40时,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试驾时间,确保车辆状态良好。其次,熟悉车辆智能安全系统...浏览全文>>
-
预约宝马X1试驾前,建议提前通过官网或电话联系4S店,确认车型库存与试驾时间。到店后,先与销售顾问沟通需求...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 DM-i试驾预约流程如下:首先,访问比亚迪官网或关注官方公众号,进入“试驾预约”页面。填写个...浏览全文>>
-
试驾奇骏时,建议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提前预约专业试驾路线,熟悉车辆性能;其次,注意检查车辆外观及内饰是...浏览全文>>
-
凯迪拉克CT5预约试驾,从线上到线下,体验顺畅而专业。只需几步简单操作,即可在官网或App上选择心仪门店与时...浏览全文>>
-
预约东风富康试驾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1 官网或官方App:访问东风富康官网或下载其官方App,进入“试驾预约...浏览全文>>
- 比亚迪海豹05DM-i试驾预约流程
- 云度新能源预约试驾有哪些途径
- 阿维塔07试驾预约,体验极致驾驶乐趣
- 宾利试驾,快速操作,轻松体验驾驶乐趣
- 全顺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QQ多米试驾预约,轻松搞定试驾
- 零跑C10试驾的流程是什么
- 宝马X1预约试驾,4S店体验全攻略
- 试驾QQ多米,畅享豪华驾乘,体验卓越性能
- 江铃集团新能源试驾预约,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试驾雷克萨斯ES如何快速锁定试驾名额?
- 兰博基尼试驾预约有哪些途径
- 试驾五菱凯捷有哪些途径
- 力帆预约试驾,一键搞定,开启豪华驾驶之旅
- 极石汽车试驾预约,4S店体验全攻略
- 本田雅阁试驾,新手试驾注意事项
- 捷途旅行者试驾预约预约流程
- 昊铂试驾预约,快速通道开启豪华体验
- 五菱预约试驾,开启完美驾驭之旅
- 试驾捷豹E-PACE,4S店体验全攻略